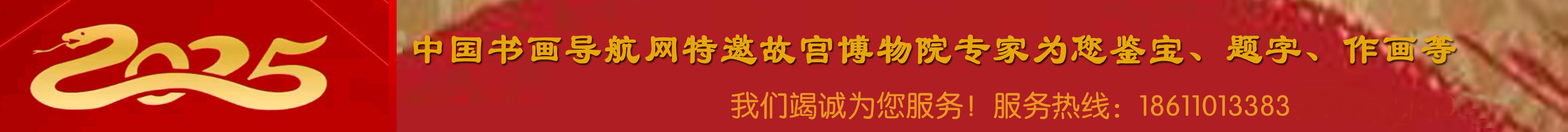我们知道,西方各国,大到都市,小到乡村,都有画廊。这些画廊需要作品来填充,作品从哪里来?从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那里来。所以说得难听一点,今天西方的美术学院在某种程度上是培养画行画的人。不过,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西方美术学院的意思,事实上,它恰恰说明西方整个社会民众文化素质的高度。在西方,并不一定是学艺术史专业的人,许多普通百姓,包括律师、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他们对艺术史都了如指掌,他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在艺术博物馆里度过的。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意大利,美术学院的教学内容已经不再是黑白素描、焦点透视和人体解剖这些古典写实艺术的创作技巧,包括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艺术风格早已进入了课堂教学的范围,甚至装置艺术、影像艺术和数字艺术也成了美术学院的教学内容。但是,一门技术一旦成为美术学院的课程就意味着它的陈旧和过时,艺术总在不断创新求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美术学院如今已经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但在我国,美术学院的作用和功能似乎比西方的更重要,它不仅承担着美术史的继承使命,同时也肩负着开创美术新路的职责。说到底,中国当下的美术学院仍然奉行的是精英教育的观念,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为美术精英,希望他们全都是创造性的人才。去年我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承担的教育部国家重大攻关课题开题报告会,课题叫做“艺术学科发展和艺术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课题研究的目标是如何推动艺术学科的发展,以及怎样建立一套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课题组考察了中国当代美术学院教育的现状并展望了世界当代美术学院发展的趋势,强调我们对新型人才需要的迫切性。他们提到作为大学教育目标的三种人才类型,就是说应用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其实就是兼具应用型和创新型两种素质的人才。在这三种人才培养的目标里,他们还是倾向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而把应用型人才排除在美术学院教育目标之外。但实际上,中国的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大多数还是应用型人才,是普通的美术从业者。我认为,如果拥有大量经过美术学院教育的从业者能够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乃至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一点不是什么坏事。[NextPage]
谈到学院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我认为这两者不是指的艺术家的身份,而是指不同的艺术观念。对于美术学院而言,永远只有两个问题,就是教什么、学什么;对艺术家来说,就是做什么、怎么做。学院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差异也是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差异还是观念。学院的本质,或者说学院的品格,最根本的还是学术。因为在西方语言里“学院”与“学术”是同一个词,就是academy.我认为对于美术学院来说,还是应该坚持以学术为本。与学术相对的概念就是非学术,非学术有很多的内容,比如政治和经济就属于这方面的东西。对学术的坚守就是要认清艺术的发展规律,并且按照这个规律,从艺术自身的出发来设计我们的课程内容,采取合理的教学方式,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专业人才。
如果说塞尚的形式主义问题不能也未能从美术学院找到解决方案,那么自杜尚的观念主义艺术产生之后,学院教育更是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在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艺术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艺术不再是技术问题,或者说,当代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技术的比拼而变成了观念的较量。在国际当代艺术界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就是观念与技术的分工,艺术家出创意也就是创作方案,由技术人员制作完成。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出现在装置艺术、影像艺术和数字艺术领域,也出现在表演艺术领域。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当代艺术界,不但装置艺术、影像艺术和数字艺术无需艺术家亲手制作,甚至表演艺术也不一定能有艺术家的亲自出场。
导致学院教育与当代艺术脱节和背离的本质问题在于,学院教育是艺术知识体制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产物,而当代艺术的价值和生命恰恰就在于不断打破既定的包括社会和艺术自身在内的各种体制和规范。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的根本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因为艺术创作总是扮演冲锋陷阵、开疆拓土的角色,而艺术教育始终肩负的是安营扎寨、坚守阵地的使命。
从一开始美术学院就只是一种职业教育机构,它的教学内容只能保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专业美术工作者,而永远不能确保它的毕业生成为创造性的艺术家。因此,让我们记住那句老话,伟大的艺术家是天生的,而不是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