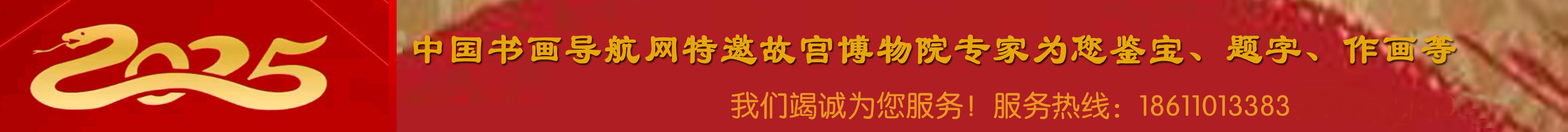闫文利/文 与画家张立一见面,我便直截了当夸她:“你真是越活越年轻,戴上红领巾,就是少年儿童!”是呀,白皙的容颜,证明人家先天是美人“坯子”;高雅的气质,说明人家后天有修为。 哎呦,跑题了。 看完张立的现场作画,听罢张立的娓娓道来,我就想:写这篇序言时,我不细说她自幼酷爱绘画,也不再夸她的花鸟画好,更不赘记她昔日众多的桂冠荣誉,一定要抛开张立那多彩的人生经历,用讲故事的方法,直述她纸上青花的“前世今生”。 故事源于 2014年春,一位老板邀请画家张立到江西景德镇,让她在素瓷坯上画最拿手的荷花、牡丹,意在获取更精美的青花瓷器。初次上阵,张立沐手静气,用毛笔蘸着稀泥般的青花料,按着国画的技法,在素坯上皴、擦、点、染起来……然而,她顿感不适。国画和青花瓷同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工具同为毛笔,画技基本相同,但作画的力道却完全不同。当她的“作品”出炉后,别人都夸挺好的,但在张立看来,水墨画家不等于工艺大师!在返京路上,张立突发奇想:“如果抛开瓷器的局限性,把诱人的青花搬到宣纸上该多好啊!” 同年夏日,张立在北戴河的一个书画院,当着华国锋夫人和女儿的面,用酞青蓝画了一幅别样的斗方月季。众人看着很新奇,立即当场装裱,悬挂在了墙上。老人久看不厌,很是喜欢,最终把这幅纸上青花收藏了。

别人的喜欢和自己内心的不满,同时叠加在一起,激发了张立刻苦钻研和努力创新的欲望。
此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立身心埋在了纸上青花里。她调制着多种颜色,寻觅着旧与新、暗与明、冷与暖的色调,试图形成深浅不同的笔韵,带来震撼人心的视觉享受……都嚷创新,但真正的创新绝非是一蹴而就的事。
看着母亲痴迷的样子,女儿用抱怨口吻说:“您就是死磕一件事!”在外人看来,那就是执着。
张立自己也说:“我就是一棵路边不计阳光雨露多少的杂草。”在外人看来,那就是顽强。
怀揣着“要干就要干到最好”的念头,张立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和对比,终于给纸上青花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换代,展现出了青花巅峰时期的精美面貌,让人更加喜爱了。

2016年,张立凭借纸上青花入选作品,跟随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到俄罗斯搞了画展。在画展进入尾声的一天,张立闲情逸致地游逛起了莫斯科红场。突然,她接到了随队翻译的电话:“姐,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列宾美术学院的院长收藏了你的画儿!”噢,列宾美术学院,那可是傲居世界的四大美院之一。人家院长能从200幅作品中选出自己的画儿收藏?张立如梦初醒后很是高兴。更让张立高兴的是,她带回了列宾美术学院院长签名的含金量极高的荣誉证书。
一来二去,张立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不知是谁还给她起了一个雅号——“北京青花姐”。因此,“北京青花姐”常被人呼来唤去,行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满足着人们获得纸上青花的心愿。 张立的纸上青花有两类:一种是宣纸上铺陈着纯正的青花,或带刺的月季、或垂挂的紫藤、或浮叶的荷花……近观,枝叶花层次分明有疏密,颜色上浓淡干湿有深浅。挂在墙上远看,洁白宣纸上泛着幽蓝,恰似一块白底青花瓷板。另一种则是,稳重的青花瓶上,随意插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或月季或牡丹,旁边辅之以盛茶水的杯子和红透了的樱桃,让你感觉静中有动,冷中有暖,煞是好看动人。

2017年,画家张立又带着她的纸上青花,随团到坦桑尼亚进行了艺术交流。一天,被多人簇拥着的他国文化部长拿着画册来了,翻到一个页面,低头看过画作,便抬头和站在跟前的画家“对号入座”握手。当那位部长翻到印有张立纸上青花的页面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啪”的一拍,依哩哇啦说了一句话,翻译道:“这个含有中国元素,这才是真正中国画!”
故事讲到这里,我猛然想到了China一词。不管它是专指“中国”还是泛指“瓷器”?然而,中国是瓷器故乡则是不争的事实。景德镇以高岭土为胎、用泊来的苏麻离青为饰而烧制成的元青花瓷,那更是创造了人间奇迹,带来了特殊的审美取向,曾作为优秀艺术与其不菲价格傲步西方市场。应该说,画家张立借助中国人、外国人对久负盛名青花瓷的奢望,让她那幽雅别致的纸上青花大获成功了。

序言写到这里,回看张立那幅我命题而作的《纸上青花一缕香》,只觉得瓷瓶上那晶亮的蓝,美得雅致;瓷瓶里那艳丽的花,美得动魄。透过画作,我感受到了画家张立所蕴含着的传统功力和创新能力。如果再见“北京青花姐”,我还想看她那行云流水般的绘画,还渴望享受她那更为精美的纸上青花。
|